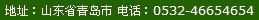|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人种、多族属、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从人种来看,早在距今—年间就有印欧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他们的混合型人种的族群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迁徙,分布在天山南北和罗布泊地区,因此新疆也被称之为人种博物馆。距今年前后是塞人、羌人、汉人、大月氏人、乌孙人、乌揭人、匈奴人等的迁徙;隋唐以后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蒙古人等形成了新的迁徙浪潮;清代之后,在不断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中,形成了近代的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的新的多元民族格局。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陆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就已成为东西方民族频繁迁徙活动的区域。至先秦时期,属蒙古利亚人种的羌人已深入到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一带,而吐火罗人、月氏人、乌孙人等印欧人种的人群亦曾一度到达河西走廊及中国北方的其他一些地区。其中后者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对于处在“丝路”中段,尤其是西域地区的古代民族构成、经济文化特征的形成等方面,曾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一)吐火罗人吐火罗人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的被认识始于国际学术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丝路”沿线考古、探险发现的各种材料的研究。在今天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曾发现了一种用印度婆罗谜(brahmi)字母斜体书写的古代不知名的语言,经过研究人们才知道它竟然属于印欧语系西支Centum语支的西北语组(North-WesternGroup),故其故乡则可能在欧洲中南部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以北,易北河(Elbe)和德聂斯特河(Dniester)之间。这种语言在东方的出现意味着曾有一支操这种语言的古老的印欧人从他们的欧洲故乡向东方发展,这些语言材料便是他们在东方活动的文化遗存。尽管国际学术界对该语言的命名尚有争论,但自年德国学者缪勒(F.W.Muller)根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中的“To?ri”一词将它命名为“吐火罗语”以来,中外学者多倾向于将吐火罗语与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吐火罗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库车、焉耆一带的吐火罗人以后才被后世称为龟兹(库车)人或焉耆人。不仅如此,通过对今塔里木盆地南缘尼雅至楼兰一带发现的佉卢文书写的古代鄯善国王的官方语言虽然是与佉卢文一体引入的印度西北俗语(IndiaPrakrit),但其土著语言却是吐火罗语。焉耆、库车一带曾流行着吐火罗语的甲种、乙种两种语言形式,而在鄯善国流行的土著语言则被称为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加之高僧玄奘在7世纪亲历该地区时明确提到这里曾经存在有一个“覩货逻故国”(今安得悦古城),所以可以推断,今塔里木盆地也曾是吐火罗人的一个重要地区。吐火罗语虽然是一种早已消亡的“死语言”,但它在语言形态上却保存着印欧语中的许多原始特征,有印欧语中的“甲骨文”之称。这表明操这种语言的吐火罗人很早就从他们在印欧人群中的亲缘部落中脱离出来,向东方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在吐火罗语流行的地区所出土的距今大约多年的干尸在体质上亦具有典型的印欧人种的特征,与中亚草原青铜时代居民的头骨形态也比较接近,它们甚至在遗传学上亦与在欧洲发现的早期印欧人遗体有惊人的一致之处。[6]所有这些均暗示出作为原始印欧人一支的吐火罗人的起源及其向东方沿后来的所谓丝绸之路发展的基本轨迹。西方学术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前年,当定居的农业人口已经占据了欧洲余年的时候,在城市文明在近东肥沃的河流谷地出现的时候,在草原和半沙漠地带发生了首次的广泛的移民运动。正如亚当斯所指出的那样,大约在前年上半期,吐火罗人从某个地区,加入到了这场移民活动,并从此与操印欧语西北语组的其他原始印欧人群(Proto-Indo-Europeans)完全脱离了关系,迁移的方向是向南或向东。吐火罗人在离开故乡以后,首先可能到达黑海大草原(PonticSteppes),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其活动轨迹构成了“库尔干文化”(KurganCulture)的一部分。马丽嘉·吉姆布塔斯认为,印欧人在“库尔干”地区渗透、扩散的第二个阶段(前—前)来自德聂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这可能与吐火罗人的迁徙活动有关。随后,吐火罗人继续东徙,经过中亚大草原,进入塔里木盆地。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ure)、阿凡纳羡文化(AfanasyevoCulture)和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Culture)等青铜器时代的文化中据认为有一部分便是吐火罗人的文化遗存。大约在前年末至前年初,吐火罗等原始印欧人群可能到达了塔里木盆地,与此相应的则是这一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印欧人体质特征的人类遗骨(体)与青铜文化遗存。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南疆西南部地区,从距今约年前后开始,从地中海东支类型为主的欧洲人群体,由西翻越帕米尔进入这一带并继续向东推进,在南疆南部边缘大约一直推进到(今)洛浦附近;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面的山前地带,大约到焉耆盆地周围。”[11]在焉耆察吾乎沟口墓地、且末扎洪鲁克墓地、楼兰北古墓沟墓地、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均发现了一批距今多年,具有典型的原始印欧人种体质特征的人类遗体(骨),他们中有的在遗传学上甚至与远在欧洲的早期欧洲人遗体存在着惊人的一致之处。他们所代表的青铜文化与中亚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亦说明了这些印欧人群前夕活动的基本轨迹,即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联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早期遗存,尤其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可能与以吐火罗人为代表的原始印欧人群的东徙活动有关。不仅如此,汉文文献中也留下有关吐火罗人在这一地区活动影响的记载,“敦薨”一词便是指称吐火罗人的一种形式。《水经注·水二》云:“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山海经》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睿发,俱东南流。径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据研究,上述敦薨之水、之浦、之薮包括的范围,当今巴龙台以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吐火罗语流行的地区。以“敦薨”命名的山川很可能便是在这一地区长期活动、影响的结果。可以推测,塔里木盆地南北部曾是吐火罗人在中国西部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汉文文献中指称吐火罗的另一种形式便是“大夏”,主要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左传·昭公元年》《逸周书·王会解》《山海经·海内东经》等先秦文献。此时,大夏(吐火罗)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山西南部一带。这里也是我们所知吐火罗人迁徙发展最东的地方。大约在前7世纪7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齐桓公西伐大夏,这支吐火罗人又退回了今河西走廊地区,并在今敦煌一带形成了一个活动中心。据研究,和“敦薨”一样,“敦煌”一词也是吐火罗的另一种同名异写形式。在今甘肃安西县东约50里,有名“兔葫芦”的地方,曾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末期、战国至秦国时期的文物;而在疏勒河三角洲之南榆树泉盆地亦有所谓的“吐火洛泉”“兔葫芦”和“吐火洛”均可视为吐火罗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影响遗存。而在古希腊著名的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志》中所记Thagouroi人和Thogara城,[19]国际学术界已公认在今甘肃西部地区,所指的亦可能是敦煌地区的吐火罗人。秦初的河西走廊主要为月氏和乌孙两大游牧势力所占据,吐火罗人可能仅仅局促在走廊西部的敦煌一隅。这两大势力的频繁征战又压迫吐火罗人沿天山北麓西迁至中亚伊犁河、楚河流域,亦即所谓的“塞地”。今天山北麓东段伊吾县境内的“吐葫芦乡”之名,可能就是吐火罗人西迁过程中的影响遗迹。迁到“塞地”的吐火罗人在希腊文献中被称为“Togouraioi”,其活动区域已经到达了今伊塞克湖周围。前—前年左右,在匈奴的不断打击下,大部分月氏人被迫放弃自己的河西故地,沿天山北麓西迁到今中亚伊犁河、楚河流域。[22]月氏人的到来又直接导致了活动在“塞地”的吐火罗人及塞种诸部的进一步西徙。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包括吐火罗(Tocharoi)在内的Asii、Gasiani和Sacarauli四部游牧集团曾活动在锡尔河北岸一带。大约在公元前年前后,由于这里又被塞种人占据,这支吐火罗四部集团被迫越过阿姆河,进入了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西北),在此过程中,他们消灭了由当地希腊人后裔所建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aeco-BactriaKingdom),并很快定居下来。故张骞在公元前年左右到达这里时,称吐火罗人所建立的国家为“大夏”,而这一地区亦因之为后世称为“吐火罗斯坦”(Tukhāristān),玄奘则称之为“覩货逻国故地”。吐火罗人是最早沿丝绸之路向东方发展的原始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尽管由于年代较早,有关他们早期活动的情况在东西方各种文献的记载中大多被湮没,但他们早期的迁徙对于“丝路”沿线,尤其是西域地区各绿洲城郭国的形成、早期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随着吐火罗人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其在早期“丝绸之路”开通中的作用无疑将被人们重新认识,有学者则称吐火罗人为“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参考文献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yaanzx.com/yasly/9444.html |
当前位置: 雅安市 >新疆史前古代民族1吐火罗人
时间:2021/6/2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雅安政务微博服务能力指数,全国前50
- 下一篇文章: 五一片单宅家每天连看三部有多爽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